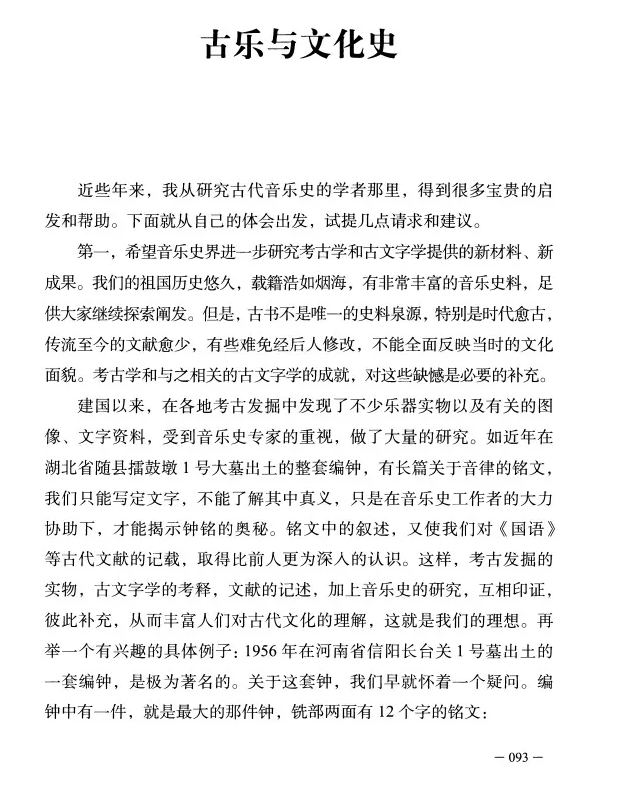
近些年来,我从研究古代音乐史的学者那里,得到很多宝贵的启发和帮助。下面就从自己的体会出发,试提几点请求和建议。
第一,希望音乐史界进一步研究考古学和古文字学提供的新材料、新成果。我们的祖国历史悠久,载籍浩如烟海,有非常丰富的音乐史料,足供大家继续探索阐发。但是,古书不是唯一的史料泉源,特别是时代愈古,传流至今的文献愈少,有些难免经后人修改,不能全面反映当时的文化面貌。考古学和与之相关的古文字学的成就,对这些缺憾是必要的补充。
建国以来,在各地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不少乐器实物以及有关的图像、文字资料,受到音乐史专家的重视,做了大量的研究。如近年在湖北省随县擂鼓墩1号大墓出土的整套编钟,有长篇关于音律的铭文,我们只能写定文字,不能了解其中真义,只是在音乐史工作者的大力协助下,才能揭示钟铭的奥秘。铭文中的叙述,又使我们对《国语》等古代文献的记载,取得比前人更为深入的认识。这样,考古发掘的实物,古文字学的考释,文献的记述,加上音乐史的研究,互相印证,彼此补充,从而丰富人们对古代文化的理解,这就是我们的理想。再举一个有兴趣的具体例子:1956年在河南省信阳长台关1号墓出土的一套编钟,是极为著名的。关于这套钟,我们早就怀着一个疑问。编钟中有一件,就是最大的那件钟,铣部两面有12个字的铭文:
惟荆历屈夕(楚国历法的二月),晋人救戎于楚境。[1]
我们觉得这不过是铭文的开头两句,文字并没有完,然而后面的钟上却不再有字了。仔细观察编钟,我们又发现这最大的钟的纹饰,虽同其余各件相似,实际并不一样。最近听说,音乐史界学者就长台关编钟进行深入研究,指出其最大一钟音值与其他有所不合。这确证编钟是拼凑在一起的,恰与我们的推断相合。
上面谈的是已解决了的问题。在考古学和古文字学中,还存在很多谜团,有待音乐史工作者协助我们去打破。
比如说,《尔雅·释乐》说:“大钟谓之镛。”《说文》的说法相同。镛是先秦古书中常见的乐器,它是什么样子呢?陈梦家先生在《西周铜器断代》中提出:
今暂以此名殷末周初的大型钟。花纹多作繁复的或变形的兽面纹,亦前后面各一,其方向是以口上甬下为顺。尺寸有甚大者,未见有铭文,亦未见成组者。甬端有时是不整齐的,并非铸后折断,乃是铸时即如此。这因为这种镛是口向上的,甬端是植于座中的,因此不需铸平。[2]
陈氏描述的这种青铜乐器,这些年屡在两湖江浙发现,但它真是文献所说的镛吗?
商代甲骨文、金文里都有“(庸)”字。这个字上半从“庚”,“庚”是象形字,是一件钟形乐器用绳索挂起来的样子。由此可见,真正的镛应该和石磬一样,是悬挂演奏的,其口部应当朝下而不是朝上,商代已经有了这种乐器。那些口部向上、甬端倒植座中的青铜器并不是镛,多数学者称之为大铙,是比较妥当的。口朝下的钟的实物,迄今发现最早的属于西周中期。因此有一种流行观点是,口向下的钟是从口向上的铙发展来的。上述古文字学的分析与这一观点相矛盾。所谓铙是怎样演奏的?铙和钟究竟是否同一乐器种类的不同发展阶段?这是我们要向音乐史专家请教的问题,希望能根据新发现的材料,进一步作出研究。
这仅仅是一个例子。相信类似这样的种种问题,在音乐史工作者和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专业工作者的通力合作下,都会逐次得到解决。
第二,希望能着重探讨古代文化的统一性和地域性问题。我国自远古时期就是一个幅员广阔的文明国家。晚清以来,学术界有一种偏见,以为夏、商、周三代王朝的范围是相当狭小的,限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主要是当时考古工作没有开展,有关古代遗存的文物只在黄河中下游少数省份发现。近几十年,随着文物考古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人们的眼界逐渐开拓,知道商周王朝的统治区域是很辽阔的,在王畿外有诸侯,其周围还有附属的大小方国。中原文化经常与周围地区的文化交流融汇,彼此互相影响,互相沟通。所以,古代文化的统一性和地域性,是文化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我们非常希望音乐史界在自己研究中能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对整个古代文化史的探讨作出重要贡献。
这里有一系列问题,有待研究音乐的学者来解决。例如人人都知道《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集,本来是能够形之歌咏的。原来的曲调固然早已失传了,后世还编了种种“诗经乐谱”,付诸实际的演奏演唱。《诗经》的十五国风,地域分得很细,像卫国,就按照武王伐商后的分划,区别为邶、鄘、卫三国。这种分国的排列,不是后人强加的,是原来固有的。近年在安徽省阜阳双古堆出土的汉初竹简本《诗经》,就是按国别分篇,和今本一样。可以设想,十五国风代表了十五种地方曲调,好像今天我们讲梆子,有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山西梆子、陕西梆子等等。这说明,诗有着鲜明的地域性。
但是,我们同时必须注意到,十五国风又有着非常明显的统一性。这十五国,由西到东,由北及南,纵横千里,然而它们的这些诗在用韵上却是一致的,这已经为乾嘉以来许多古音学家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在今天的方言里还做不到,比如有的山西方言就分不清-n和-ng,以致作诗词把韵脚押错了。《诗经》却不是这样。有人可能认为这是经过文人加工,也许就是孔子删《诗》的结果吧?我们认为,这种解释也是不对的。因为,从北宋到现在,已经发现了许多有韵的青铜器铭文,秦、齐、晋、楚、徐、越等国都有,其用韵仍然是一致的,而且和《诗经》相符合。这样统一的韵部分划,无疑是古代文化统一性的具体表现。
统一性和地域性是一对矛盾。我国的古代文化是居住在中国广大领土上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不同地区、不同部族的人民,其文化处于不停顿的交融过程之中,所以既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又有广泛的统一基础,我想古乐也是这样。擂鼓墩大墓编钟铭文详记曾国(我们认为就是文献中的随国)和申、楚、周、齐、晋等地律名、阶名的对应关系。究竟怎样看待古乐的地域性和统一性,这和整个古代文化的发展有怎样的联系?也是我们要向音乐史界的学者们请教的。
第三,希望不要过低地估计古代的文化水平。
我国古代文化绚丽灿烂,早为世人所公认。但近年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证明,我们过去对古代文化水平的估计,恐怕失之过低了,需要对一些传统的看法作出必要的纠正。
大家知道,历代学者对古书的辨伪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清代几位大家,目光犀利,成绩卓著,我们应当继承他们的研究成果,学习他们坚持真理、不怕打碎偶像的精神。不过,辨伪是不能过头的。事实上,有些辨伪家的工作是过了头了,也就是说,把一些真的古书定成了伪书,弃之不顾,其结果是导致了古史的虚无主义。有关古代音乐的若干史料也是如此,如果不分皂白,一概抹杀了,势必使古代音乐史变成一张白纸。
《左传》包含不少音乐史料。过去曾有人认为这部巨著是王莽的国师刘歆一手伪造的,这种论点至今绝大多数人是不相信了。40年代初,罗倬汉先生写了一本《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考证》,以大量材料证明司马迁著作《史记》依据《左传》,而当时的《左传》就是今本。后来,日本学者也做了类似的研究,其方法与罗氏相似。近年许多考古发现,都反复证明《左传》所记是古代的信史。看起来,《左传》作为史料的名誉已经得到恢复。
《周礼》也包含不少重要的音乐史料。最近发现不少周代青铜器的铭文,可以与《周礼》的记载相印证。如陕西周原出土青铜器有人名“裘卫”,官职即《周礼》中的司裘,是管理毛皮的。除了《周礼》,别的书里没有这个官名。把《周礼》作为一种重要的先秦史料来使用,应该说是不成什么问题的。当然,它不是所谓周公致太平之书。
对于某些考古材料的解释,也需要思路宽广一点。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第2册图版四,有一件燕下都遗址出土的楼阁形铜饰件。楼阁上部的女乐正在演奏一种弦乐器,从其弹拨手势看,很像琵琶。战国时代是否已有琵琶?我觉得不是不能讨论的。
这样说,并不是讲伪书都是真的,后世一切东西上古都可能有。我只是主张对古代文化的水平不可贬低,应当实事求是,如实地给予估价。
最后,希望正确看待音乐在古代文化中的地位。古人,特别是先秦时代的人们,对音乐的看法和今天我们的观点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应当了解当时人怎样看待音乐,音乐在他们的思想和生活里占据什么样的地位,给予正确的分析研究。这一点,我觉得目前做得还是很不够的。
中国古代对乐十分重视,把乐列为“六艺”之一,作为教育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音乐在当时绝不是单纯的娱乐,而有着重要得多的意义。有些论著,把古乐描写成只是贵族的淫侈享乐,这恐怕是把古乐看得太狭窄了。古人以礼乐并称,有着深远的根源。在远古的时代,宗教性、政治性的礼仪总是与音乐舞蹈同时兴起,互相联系。所谓“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有祭祀也就必然有乐舞。关于商周的礼,特别是祭祀,前人做了较多的研究,而对配合祭祀的乐舞,已有的探索便很少。事实上,商代甲骨卜辞有许多有关乐舞的记述。占卜祭祀,不仅卜问所用祭品种类多寡,也常卜问乐舞的设置。
礼和乐又总有一定的思想贯穿其间。著名的《礼记·乐记》,就是从儒家的立场论述礼乐的思想的,是一篇难得的文献。篇中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这就把乐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了。音乐是谐和的,在古人的宇宙观中,乐被视为宇宙谐和规律的体现,所以说“与天地同和”。《吕氏春秋》的《大乐》篇讲得更明白,主张音乐“生于度量,本于太一”,而太一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这种思想,在秦汉以后便不易见到。只有充分认识这些音乐思想,才能对音乐在古代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足够的估计。
附记:这篇小文中所论商代有口部向下悬挂的青铜打击乐器一点已得证实,请参看高至喜同志的《论商周铜镈》,载《湖南考古辑刊》1986年第3集。
(原载《人民音乐》1981年第6期。今据《缀古集》收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来源:出土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