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我们将儒学史研究目光投向西部时,不难发现,西部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历史积淀非常丰厚,其所积累的历史文化、地域文明,对儒家形成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相比于其他的区域儒学,西部儒学明显具有强烈的继承性、包容性、普适性、外传性和民族性,为儒家地域性发展(蜀学、关学、陇学、朔方学、滇学、黔学等)、国际性传播(丝路儒学)、宗教性融合(释儒、道儒、藏儒、伊儒等)、民族性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做出过重要贡献。西部儒学是中华儒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作者:舒大刚,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摘自:《孔子研究》2025年第2期
原题:《试论中国“西部儒学”的突出特性》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5年第9期
(点击查看第9期目录)
“西部儒学”是指在中国西部地域生长、传承、演变,并与中原儒学乃至四方互动发展,同时又具有自身特点的儒学。“西部儒学”是丰富多彩的中国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部对儒家形成有奠基性贡献
儒家学派是孔子集历史文化、八方智慧之大成而后创立的。孔子之前是否有“儒”,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如章太炎认为孔子之前已经有“儒”存在;胡适虽也认为“儒”在孔子之前就有,但他主张“儒者出于神职”;郭沫若反对胡适之说;冯友兰认为,儒是一种有知识、有学问之专家;徐中舒通过考察甲骨文中“需”“区需”等字,提出“需”字即“儒”,“区儒”即“大儒”,使得“孔前有儒”说得到进一步“证实”。以上诸说均有一定依据。至于儒家学派,金景芳认为,有经典传授、有理论纲领、有徒众群体的儒家学派,必至孔子行教时才真正开始。“经典”“理论”和“徒众”便成为衡量“儒家”是否形成的基本标准。
1907年,谢无量《蜀学会叙》又提出“原始儒学,禹创”的说法。他认为“伏羲画卦,神农重卦之象”,神农后有《连山》《归藏》《周易》,是谓“三易”。其中“ 《连山》,禹制之”,即第一部“易经”由禹创作,“汉时藏于兰台”,当时桓谭还“亲见《连山》”,说有“数万言”,“当是禹所为”,其书久佚,只有扬雄《太玄》,张行成称其“拟《连山》者”而成;《归藏》今天也湮没无闻,不过“宋初犹存,然无通之者”,“独后周卫元嵩造《元包》,明其学”。可见易学既是“兴于西羌”的大禹所创,又由西蜀易家扬雄、卫元嵩等人所传承,而且影响到《周易》的形成,成为易学源头。
谢无量又说:“儒家者流,明尊卑贵贱之等,叙仁义礼智之德,察于吉凶祸福之乡,称天以为治,其原盖出于禹。”这些都体现在《洪范》中,《洪范》是自大禹时就传下来的。他还特别指出,“ 《洪范》‘初一’至‘六极’六十五字,刘歆以为即《洛书》本文也”,并将伏羲得《河图》制八卦和大禹利用《洛书》制《洪范》相提并论。《周易》可理解为哲学论、方法论著作,《洪范》是行政学、政治学著作。也即,大禹为儒家诞生准备了哲学经典《周易》和政治经典《洪范》。加之大禹之后开启“父传子,家天下”的小康之世,中国国家制度奠基于此,孔子将儒家称道的孝道伦理、礼乐文明、水利重农等都归功于大禹。可以说,大禹为儒家提供了经典、理论和理想制度的基础。
沿着谢无量这一思路,我们会发现,儒家经典中《诗经》之“豳风”“秦风”“周颂”及“二南”“二雅”之大部分,《尚书》之“夏书”“周书”,由“周公制礼作乐”而形成的《礼经》《乐经》,始于周官史职而形成的《春秋》,都源自西部地区。由此可见,孔子之创立儒家,正是利用了尧舜时“司徒之官”所守教化之义、“周礼尽在鲁”的历史积淀和“夷俗仁”等地域文化的多重资源,才确立起以“六经”为载体、以“仁义”为理论的思想流派。儒学既有对周公以来的包括西部在内的历史文化的传承,也有对包括齐鲁等地域文化甚至蛮夷戎狄等民族文化在内的多种文化的吸收。
西部儒学具有突出的继承性
儒家伴随孔子“删订六经”“周游列国”以及孔门后学传播经典于各地而不断发展壮大。“西部”在儒家形成过程中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早在孔子授徒时,就有秦祖、壤驷赤、石作蜀、燕伋、商瞿上四位学徒来自西部,《周易》《尚书》《诗经》等经典在西部也得到初步传习。
随着秦国历代君主励精图治,招揽了儒生、墨者、纵横、名、法、兵家等大量东方人才,东方经典文献也随之入秦。吕不韦组织编修《吕氏春秋》,其中《当染》《劝学》《孝行》《音初》等篇就包含了大量儒家作品和思想。秦始皇统一全国,定都咸阳,四方儒生咸集关中,七十博士而儒居其半,后虽然发生“焚书”“坑儒”事件,但儒家“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等思想早已融入大统一后的秦制之中,秦朝博士制度也为后世的经典传承播下了火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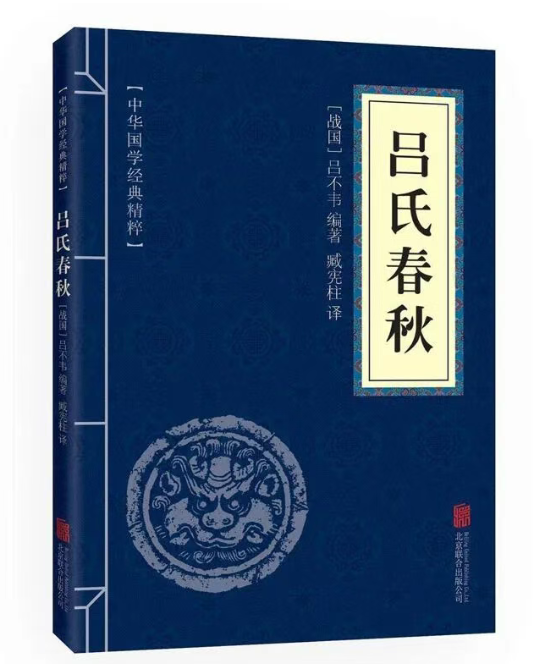
在较为偏远的地方,特别是在秦国于公元前316年占领的巴蜀地区,民间犹有儒经收藏,流传有秦儒“二酉藏书”的传说,也有胡安隐居邛崃白鹤峰传经、犍为舍人首注《尔雅》、林闾翁孺传“輶轩语”、司马相如从胡安受《周易》等事迹。正因为西部存在民间藏书和通经隐者,汉初“除挟书之律”后,古书旧籍乃逐渐现世,隐士名儒也慢慢现身。
汉景帝末年,庐江舒城人文翁守蜀,见蜀地僻陋,于是肇启学宫,征下县子弟入学,传授“七经”;通经之士可以绩优入士,弟子张宽仕至庐江太守,开启了儒学官学化、学而优则仕,甚至科举考试、文官制度的先声。此外,西部儒学还以经典教化为本,积极发挥“淑世济民”和“移风易俗”功能。对此,史称“文翁立学、兴教化蜀”,于是蜀地大化,移风易俗,蛮夷之风丕变,而且人才辈出,推动地方学术兴起。仅在蜀地,就涌现出王褒、落下闳、严遵、扬雄、何武等长于经学、文学、历学、玄学诸领域的学人,因而这一时期史称“蜀学比于齐鲁”。
从此,西部以官方办学和民间私塾等多种渠道,参与推进了传统中国以儒治世、以经议政、礼主刑辅的进程,儒学也在为政治和世俗服务的过程中,得到历代传承和不断更新发展。
西部儒学具有广泛的包容性
西部地广人稀、南北纬度跨度大、民族成份多样、社会形态复杂、文明程度参差不齐、文化形态多种多样,这就势必造成学术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包容性。各民族在西部生产生活,多种信仰在西部传承演绎,儒家学说也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在西部传播、演进。
如西汉司马相如就率先提出“兼容并包”“参天贰地”的治理观念,以及“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创作理论。之后西部又出现严遵、扬雄的博采诸子,赵蕤、苏轼的诸学互补。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鸠摩罗什到长安后传译大乘般若学,玄奘在成都慈恩寺(多宝寺)受具足戒,道经丝绸之路前往西天取经,归来后在大雁塔翻译唯识学,于是长安、成都等西部城市成为较早的求法取经与佛经传译和刊刻中心。自后,更有宋陵阳龙昌期、新津张商英、咸阳人王重阳积极提倡“三教合一”,宋普州崇龛人陈抟、凤翔郿县人张载的儒道合流,宋蒲江人魏了翁、明新都人杨慎的汉宋皆治,明代藏传佛教领袖宗喀巴、清代伊斯兰思想家刘智等人的“儒佛”“伊儒”结合,晚清民国威远人段正元、彭州人尹昌衡的“五教同德”,当代四川井研人、哲学家萧萐夫“集杂成纯,漫汗通观儒释道;多维互动,从容涵化印中西”的庞大学术气魄,以上这些都体现了西部学人博大宏阔的治学风格和学术气象。
西部儒学具有广泛的普适性
中国疆域辽阔,人群众多,如何和谐地治理域内域外各个群体呢?大禹所传《洪范》有“会其有极,归其有极”之说,宋人胡瑗《口义》中将其解为“以四海为一家,以万民为一人,其情则天下同也”。由于夏禹的巨大功德,故而他受到中原及四海各部的尊重、拥戴。对于这位“兴于西羌”的先圣,孔子及其儒家也对其赞赏有加。中华文化向来主张不以血缘分亲疏,而以文野定褒贬,奉吾教者皆吾主,爱吾民者是吾君。因此,大禹便成了西部各地信奉的“禹王”,自然而然就成为加强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力量,为各族接受儒学、形成共同信仰做好了准备,同时也为后来西部呈现出各种形态的“地域儒学”奠定了基础。

大禹
如在十三朝古都所在地关中地区,形成了父天母地、民胞物与的“关学”;甘州、肃州虽然远在西陲,但亦知“庠序之设,教育人才,风化之本,其道甚重。自汉迄明,科条渐备”,形成“陇学”;在巴蜀地区,早有“蜀学比于齐鲁”之称;在贵州地区,“黔自元以前本属苗徼,自明以后始渐被文明”,清雍正后,恢复学校教育,大兴教化,至晚清号称“西南邹鲁”,蔚为“黔学”重镇。云南地区,兴学更早,“滇南建学,肇自汉时。张(宽)、盛(览)受业长卿,尹(珍)、许(慎)执经中土,滇之文风,由此渐启”,流风所扇,渐成“滇学”。再有,儒学又与传入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教义结合,形成伊魂儒里的“伊儒”;儒学与藏地的藏传佛教结合,形成了喇表儒心的“藏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西部多元一体的区域文化,与儒学互相结合、彼此融合,强化了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促进了民族团结和边防稳定,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儒学发展样态。
西部儒学具有突出的民族性
儒学自古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源泉。西部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儒学在历史上长期与周边四夷的思想观念、文化意识相互交流与互相融合,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民族儒学”。
自汉以后的“南中大姓”,五胡十六国时期在西部建都的少数民族政权,无一不在既得社稷之后,兴行儒教以巩固政权;唐代南诏、大理,以及西域各国,更时派子弟前往长安或成都学宫研习儒家经典和中原文化。明代平定宁夏后,置兵卫,设学校,兴教化。清同治时,在平定陕甘、新疆的回汉冲突后,有官员建议办学兴教,互通婚姻,秉公执法,持平办理,无疑对民族共同体形成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从晚明到清,儒学又与伊斯兰教哲学思想结合,通过贯彻宋明理学思想文化精神来阐释伊斯兰教经典、教义和哲学思想,形成了“附儒以行”或“以儒诠经”的儒伊形态。13世纪的《萨迦格言》汲取了藏族世俗伦理观念、藏传佛教义理思想和中原儒学文化精神,融会贯通而成为藏族社会和民众的“格言”。
特别是在民族丛居、伊斯兰教盛行的新疆地区,当地政府通过设立学校,聘请师儒,讲解经典,演习礼乐,讲练技艺,勉励道德,择材而举,于是“道足济时,而泽足垂后世”,皆因“教之者能端其本,故受之者自相感以诚耳”。
唐宋时期,白族先民的社会中已逐渐形成既信奉佛教又尊崇儒学的文化风气,并产生了“儒释”“释儒”或“师僧”群体。“释儒”哲学是白族这一民族群体在形成发展和观念探索中逐渐生成的基本思想形态,其理论成长的内核是佛儒的融合。
由于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学传经,儒学“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天地人合一”等观念,也被羌族、壮族、瑶族、黎族、白族、彝族、纳西族、苗族、布依族等民族吸收,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民族伦理和民族宇宙观。西部儒学突出的民族性,促成了儒学与少数民族思想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流交融。
西部儒学从历史事实、政权互动、文化认同、风俗同化等多个方面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发展与铸牢的不竭源泉。
西部儒学具有开放性和外传性
儒学在西部两千余年的流传演变史,也是儒学在丝绸之路传播、影响的历史,无论是在北段丝绸之路,抑或南段丝绸之路,都可以找到儒学传播的痕迹。
汉开西域,朝廷派驻官兵以及随军家属前往,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也随之深入到西域各地。吐鲁番出土的唐西州文献中就有“义学生”“私学生”等记录,这表明古代西州效仿汉人私塾,私家学习儒家经义。另外,吐鲁番人注重儒学教育的历史证据还体现在墓砖、蒙书以及人名、地名等上。
清代,儒学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新疆图志》载,清朝建立以来,在镇西、迪化等地,由于旗人和汉人较多,学校开始兴起。乾隆后,更多县份增设学校。光绪初年,左宗棠上奏改设郡县,设立学塾以潜移默化教育儿童,刘锦堂进一步在伊犁、疏勒、温宿等地开展训导。于是,在吐鲁番、乌苏精河与夫拜城、焉耆、沙雅等处,学校日益兴盛。儒学在古代西域的广泛传播与影响促进了汉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同时也促进了西北丝绸之路沿线民族对汉文化、大一统的认可与接受。
南丝绸之路以成都为起点,纵贯四川、云南,一直南下延伸到印度、缅甸等南亚、东南亚国家。经由南丝绸之路,儒学在我国境内与云南各少数民族思想文化发生了碰撞,境外与缅甸、印度、越南、泰国等思想文化相互交流,共同构成了丝路儒学的重要内容。
结语
儒家是孔子集虞、夏、商、周文化之大成,总四面八方之精神而后形成的博大包容的学术体系。在儒家形成后,儒学又经历了两千五百多年在南北东西各地的流传,在这绵长的时间中和广袤的空间内,儒学发生了相当复杂的历史演变和创新发展。当我们将儒学史研究目光投向西部时,不难发现,西部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历史积淀非常丰厚,其所积累的历史文化、地域文明,对儒家形成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相比于其他的区域儒学,西部儒学明显具有强烈的继承性、包容性、普适性、外传性和民族性,为儒家地域性发展(蜀学、关学、陇学、朔方学、滇学、黔学等)、国际性传播(丝路儒学)、宗教性融合(释儒、道儒、藏儒、伊儒等)、民族性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做出过重要贡献。西部儒学是中华儒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儒学宝库中的明珠。
来源:社会科学文摘

